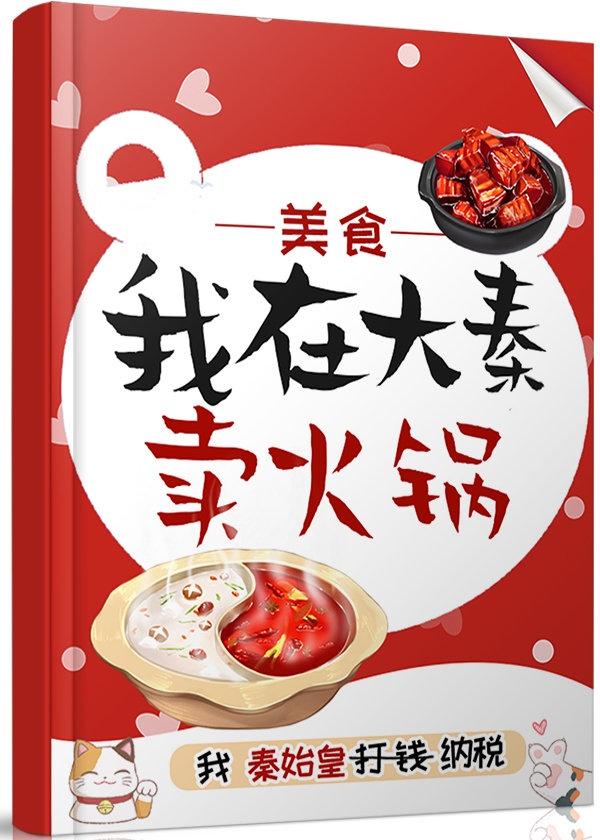2 你是谁(第2页)
禅房花木深,孟洛宁来这儿做什么呢?一瞬间,她好奇心泛滥,想要进去一探究竟。
想到,也就这么做了,走过去,毫不犹豫地推开了那扇门。
一间狭小的暗室,光线幽暗,入门即见一张供桌,供桌上摆满了正燃着的莲灯,再往上是供台,竖立着一盏牌位,牌位两旁水养着两瓶桃花,已经萎靡了。
冥冥之中,秦烟总觉得那盏牌位和自己有牵连,她慢慢走上前去,看牌位上的字。
“阿馥之灵位。”
刻字的凹陷处呈现褐红色,总觉得哪里怪怪的,借着烛光,秦烟凑得再近些,牌位上刀痕累累,一横一竖都不着力,不像是匠人手笔。
“阿馥……”
秦烟喃喃念着,蓦然瞪大眼睛,抬手捂住嘴。
如果不是先遇到了孟洛宁,纵然看见上面的名字,她也不会想到在古寺深处的禅房中供奉的是她自己的牌位。
阿馥……阿馥……这是她的乳名,从小,孟洛宁就是这样唤她的。
他疯了吗?
王馥是昭告天下的皇后,死后定然也是以皇后之礼入皇陵,他私下里供奉她的灵位,时时前来悼念,若是被人现了,被有心人拿“皇后与外男有私情”
来作文章,她王家,他孟家,恐都要遭受牵连。
他怎么就这样单纯?
以为牌位上没有她的姓氏,别人就猜不到了吗?
封后前,王家五姑娘与孟二公子青梅竹马感情甚笃的流言在宫中四起,皇后是不是孟洛宁青梅竹马的阿馥会有谁在意?看重的还不是前面那个“王”
字。
父亲王岩当时已位列三公,若他的女儿成了皇后,朝之重臣,再加一个“外戚”
的名头锦上添花,权势可滔天。
她的婚姻,她的后位,不过是权力博弈中的筹码罢了。
她活着时一步一步,要走得小心翼翼,她一死,仍然万事难休。
她还有一双儿女,不能冒这个险。
正待她拿不准该怎么办时,孟洛宁回来了,捧着一大束鲜妍的山桃花。
见着她先是吃了一惊,而后眼睛里盈满戒备,声气森冷,“你怎么在这里?”
秦烟定了定神,站在从门缝泄进来的光束里,不卑不亢地扬起脸,“若这扇门在公子离去时就已经上了锁,那此刻,我也就不会站在这里了。”
孟洛宁一瞬明白了她的言下之意。
她在提醒他太过大意。
心念电转,他望了望供台上的灵牌,倏又想到,她又是如何知道他太过大意?
“你认识牌位上的人?”
秦烟也将视线移向牌位,“‘馥’意指出众不凡,能担得起这个字的,又让公子念念不忘的,能有几人?重要的不是我识得不识得牌位上的人,而是,如果我能认出她是谁,其他人也能认出来。”
孟洛宁的神色一下肃穆起来,还伴着些许难堪。
秦烟鬼使神差伸出手,抚触牌位上的字。
“人死了,就是一把骨,沧桑聚散,转眼成空,哪还听得懂活人说什么?做给外人看的规矩,有没有都不重要。
怕只怕,死后都被吵得不得安宁,今日父母来哭,明日子女来哭,后日亲朋旧友来哭,吵也要吵死了。”
昏朦光线里,秦烟的侧颜像极了那个人。
孟洛宁心头一动,脱口而出,“你是谁?”
秦烟回头,凝视着他的脸,“我姓秦,秦烟。”
她把已经编好的草蚱蜢放到供台上,蚱蜢的眼睛绿豆大小,用力瞪着,活灵活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