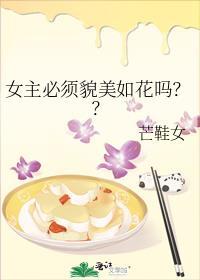第149章 换了芯子(第2页)
冯葭将脸上白巾褪下,露出一张美脸,远处灯笼打在她莹白肌肤上,透出点病态白,点头道:“臣女也样想。”
时旬叹道:“太平教朝忌讳,件案子得从长计议。”
冯葭:“臣女担心另外一种事。”
她上前两步,秀眉微蹙:“想必大听过邪教往生阵。”
时旬点头,想起大理寺案牍。
上头曾记录邪教一种阵法,此阵以至亲血阵,间隔四,凑齐一心五肢,便可开启大阵,名往生,可使死复生。
可在时旬中,什凡长生,逝者复活,过就蛊惑世手段罢了,而当年太平教主巽寮,也只过个招摇撞骗,自掘坟墓道士而既然知道往生阵,必然也知道,开启此阵一个必然条件。”
夜中,冯葭背靠紫藤,一身青衣飒而立,清风拂面,几株花落在她头,时旬手指动了动,最忍想将那花取下冲动,道:“被复活者必须尸身保存完好,且作此阵必死者至亲?”
冯葭点头:“臣女前打听过,覃死,尸身被其兄长领,那所线索都指向一个,那就巡。”
时旬看了她许久才收视线:“你意思,那个叫巡邪教徒?”
冯葭道:“臣女也猜测。
周慕琪与覃死脱了干系,作巡兄长,自然大理寺如此草草了案,所以蛰伏一年前复仇。”
“仅如此,他想复活唯一妹妹,所以巡先将周慕琪绑架,拔掉舌头,扔在枯井,而又以银簪刺破顾院长双肺,掏其心脏,可往生阵需要一心五肢,那谁下一个目标呢?就臣女担心!”
“而且,臣女心中一直疑问。”
“说听听。”
冯葭道:“大记得奉上银簪吗?那就在。”
她以脚点画了一个圆,“在里,被一女学生撞倒,而那女子慌乱间掉落了一本书,书中便夹着那只银簪。”
“女子?且顾家塾女学生?”
“错,”
冯葭道,“只那匆忙,又正好下学时辰,往甚多,那女子从臣女身边过,只侧目看了一便匆匆离去,所以臣女并未看清她长相,只记得她身量很高。”
她伸手比划了一下:“大概高。”
“所以臣女一直想明白,此案极大可能巡犯下,可他个男子,那书院女子又谁?”
那何藏凶器?她与巡什关系?说犯案实际两个?那那个女子又在案子里扮演何种角,她也了覃报仇?她又覃什?巡现在又藏匿在哪?
种种谜团萦绕在冯葭心头,百思得其解,她总觉得自己好像忽略了什东西。
时旬抬头看了一夜,月上中天,子夜,“巡事,本官明便奏请三司衙门协助调查,时辰早了,本官先送九姑娘去。”
冯葭看了天,确实很晚了,她又将白巾重新系在面上,福了福身子:“必劳烦大了,马车就在外候着,臣女自己去。”
说完便转身离去。
待她背影转出门外,马车也消失在夜幕中,时旬才转过身对着黑暗中拱手拜了拜。
李蕴玉从黑暗中走出,他穿着破布麻衣,脸上粘着白和胡须,可此刻佝偻背脊&xeoo挺直,手背身,贵气难挡。
“个谢九能快在谢家站稳脚跟,可见智谋双全,而且她对大理寺审案步骤了若指掌,对案件分析独到辣,石城并如此本事,无师自通?太过牵强,实在可疑。”
李蕴玉答,只微微轻抬目光。
时旬&xeoo又轻轻摇头:“可派去石城探子拿着她画像暗自调查,她确实谢家养在外面十三年庶女,谢兰昭,容貌一致,并未被替换。”
李蕴玉看着夜出神。
可若谢兰昭模样变,里头换了芯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