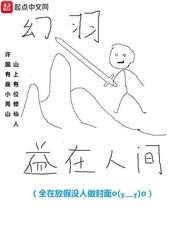第四章 白色鸦片(第2页)
是因为一开始对她心动之前,先动了恻隐之心吗?还是因为每个人都有一部分自我一直处于另外一个世界,那个自己无法抛弃的世界?
不得不承认,那一部分也是重要的部分,我们每个人都有理智的一面,也有疯狂的一面,每个人都在这两部分之间进去拉扯、协调,关于这一点,卡森一开始不信,但现在却不得不承认。
两人喝着香槟,相拥站在窗前,看雪花从空中一片一片地飘落,耳鬓厮磨之时,卡森问:“为什么你这样爱雪呢?”
“当时还在阿拉木图,你记不记得,我过生日的那天,你给我打电话了。”
“嗯。”
“那天很冷,雪很大,可我听见你的声音,觉得很甜,一点也不冷。”
卡森非常开心地笑了:“所以,那个时候就爱上我了吗?”
薇不好意思地脸红了,如今自己身在这白色鸦片包围的雪景之中,有所爱之人在旁,再没有了过去爱所带来的怀疑、揣测、背叛,控制,只有他的全部的爱,真是鸦片,令人迷醉,叫人不省人事。
在爱的同时,薇喜欢冷,因为这叫人清醒而不至于失去理智。
雪很大,让人的视线一片模糊,卡森的思绪飘到了别处,不禁皱起眉头。
在康提城内,某座不知名的桥上,有个气质独特、让人一眼难忘的女孩曾对自己说:“因为喜欢在阳光底下生活,所以我一定要住在热带地区,你说,这样是不是就能离太阳近一点了?”
那时候她带自己去佛寺献花,去山上采摘红茶,一起去看壮观的象群、行踪飘渺的锡兰豹、绚丽多彩的鸟儿,两人几乎吃遍了城里的知名、不知名小店。
从科伦坡中央车站开往南部古城高尔的海上火车上,印度洋的海风微微拂面,蔚蓝大海近在咫尺,如梦如幻,那一路留在自己心底的,不只是人们的欢声笑语,还有那永不能令人遗忘的她,那能让世界上所有繁华都市女郎失去光芒的纯真笑脸。
她喜欢在住的地方嬉水,修长纤细的小腿赤裸着,像白鹤的腿一样纤细纯净,粘着蓝色睡莲的花瓣,白璧无瑕,她是属于绿野的,浑然不知自己是那种越素越清冷、美丽的人,那双深邃的细长眼睛,永远在勾着你,却又永远看不上你。
在这样冷的地方居住和生活,身边有深爱的未婚妻,仍然会毫无预兆地想起喜欢热带的她,卡森清楚自己早已经不再爱她,但是仍然放不下她,这到底是为什么?
是因为上次和薇在艺博会上偶遇黎先生的缘故吗?
那次艺博会上的闲聊,让卡森知道了南芳的过往,她的小时候以及她和阮文森、金正康之间的事,虽然早已时过境迁,可是卡森无法欺骗自己的良心,那就是自己曾经因为误会和愤怒,没有给过她解释和澄清的机会,单方面结束了和她的感情。
为什么过去没有相信黎震说的话,而现在却相信呢,也许是因为人在气头上听到的解释都会认为是对方在诡辩,曾经以为人的记忆、那些甜蜜的过往会欺骗自己,所以宁愿相信眼睛所看到的,但却从未相信过她的心,真正的她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人,那些碎片般的有关她的片段在脑海中,终于拼凑成了一个完整的她。
而这个她,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
离开康提之后,卡森一直有种阳光亡失之感,这种因为伤害她而受到良心谴责的愧疚日日夜夜、悄无声息、毫无预兆地跳出来折磨着卡森,这不能说出的类似思念的东西,犹如病毒一样可怕,她到底去哪儿了,这句话日日问,夜夜问,却得不到回答,让人寝食难安,日渐消瘦。
这过期的爱情病毒,真让人难受,尤其是在自己和薇越来越好的时候,她的身影总是无时无刻出现在心间,她好似还像过去那样,拥有莲花般纯净自然的笑容,在对着自己笑。
薇因为遇到卡森,从此再也不专画人物,转而痴迷没有人物的自然,作为一个青年画家,薇一开始就是自由主义,从不试图成为第二个谁,也不存在从群体中抽离出来寻找个人意义和价值的自我创造,一直以来,只想通过某种生活方式或艺术形式尽可能自由完整地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