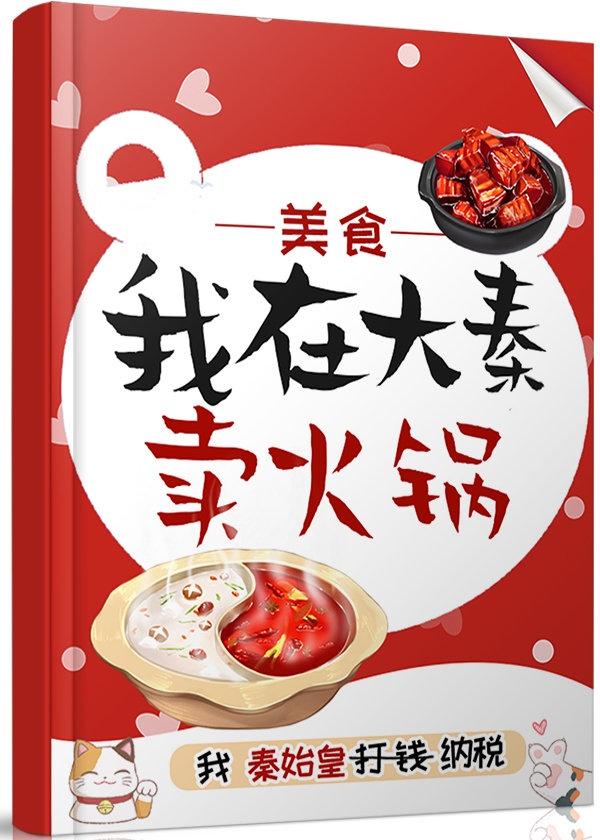第一章前六门死(第1页)
我叫陈晨,外号陈九指,因为早年在一家电子游艺赌博厅里的打鱼机上作弊,被老板抓了个现行,被剁去了一根小拇指,故此得朋友调侃。
说不上是什么时候迷上了电子赌博机,我的整个青春都与那该死的东西形影不离,一点儿也不吹的说,只要是市面上你见过的赌博机,我全都能不费吹灰之力的给打出爆机。
故事就从我十五岁那年说起。
记得那是一个冬天,学校旁边小区的紧里头,有家不起眼的游戏厅,我经常逃课去那玩,那时候kof97,98简直是风靡到不行。
有天下午,我兜里就剩下一个游戏币了,准备再打一把kof97通全关,正在这时,跟我一个班的铁哥们陆小胖,气喘吁吁地跑到游戏厅给我通风报信儿:“陈晨,班主任可说了,下节课你要是再不出现,就要找你家长啦!”
我一听,慌了,家里管我特严,赶紧跟着陆小胖就准备拔腿往学校跑。
可当我俩跑到门口的时候,看见了一台赌博机,闪烁着光亮,老觉得手里握着的一个币子扔了可惜,因为怕班主任对我搜身,所幸就对陆胖子说:“等下,我押一把。”
这是我第一次碰赌博机,一个币子投进去就是10分,可以压八门任选,除了大奖和苹果之外,还有大三元(大7,双星,西瓜)小三元(铃铛,橘子,芒果)。
我毫不犹豫的每门压了一分,额外在大奖上压了三分,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按下了启动键,也不知道是走了什么狗屎运,赌博机突然爆闪,红黄绿三色彩灯闪烁交错,伴随着动感的dj,机械般的女音响起:“恭喜您中奖九莲宝灯。”
这动静一出,几乎是游戏厅里所有的人都围了过来,陆小胖则是好奇地问我:“九莲宝灯是什么意思?”
当时我也不知道,所以摇了摇头,双眼直勾勾地盯着赌博机的灯板,只见所有的灯板挨着个的亮起,中奖的分数直线往上攀升,那一刻我兴奋到了极点。
“我去,发财了!”
我激动地指着屏幕上6250分,嚷嚷出声,游戏厅的币子是一块钱五个,625个游戏币那就是软妹币125块钱,要知道那个年代,我在学校吃饭的伙食费,一个月也才刚100块钱。
我兴奋地按下退币毽,然后朝老板要了个币盒,把退出来的币子一摞摞摆好,再拿回到老板面前,果断的要求退钱。
老板很痛快的给了我钱,接着我便梗着小脖,手里掐着一张百元大钞,在一众社会小青年的羡慕嫉妒恨的目光下蹦着离开了游戏厅。
自打那以后,我几乎是天天都去,我傻乎乎的以为自己找到了赚钱的路子,就想着每天赚个一百多块钱,一个月下来比我爸妈俩人加起来的工资还要高,还上毛线的学。
然而现实往往是残酷的,高中三年下来,我粗略的算了下,大概输给那台赌博机能有将近一万块钱。
开始的时候是五块十块的输,再后来一百两百的输,越输我就越不服,越不服我就越是控制不住的要干!
现在想想可真是苦了我爸我妈,打着各种补习班的幌子跟家里要钱,伙食费和班车通勤费也都被我给输了进去。
都把心思用在了赌博机上,理所当然的高考落榜,我爸我妈对我失望到了极致,给我找学徒的工作我也不干,依旧是往游戏厅里钻,见了赌博机就挪不动步,到后来也就懒得管我了。
成了小地痞子的我,成天堵在原来学校的门口,管学生要钱,要来钱了再给游戏厅老板送去。
那是夏天的一个晚上,听一玩赌博机认识的朋友说站前新开了一家,机器是广州那边过来的森林舞会,顿时来了兴致,揣着兜里的三百块钱屁颠屁颠的我就去了。
不得不说森林舞会是个非常牛逼的赌博机,十个人人可以坐在一台机器面前玩,同时交流心得,一般也就是这把出什么动物,或者这个面是放分面还是下分面。
反正别管是会不会打分的,都能白话出一套道理来,而上面的狮子,熊猫,猴子,兔子也是雕刻的活灵活现,算得上是电子赌博机的一种全新改革,由平面换成了立体,更加的有代入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