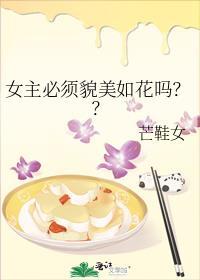第86章 帮我哄哄┃这是一种带着攻击性的帅没人抵挡得了(第1页)
第86章帮我哄哄┃这是一种带着攻击性的帅,没人抵挡得了。
岑琢做了个梦,梦里爸爸妈妈、哥哥姐姐,还有他,围在一起吃米汤,热腾腾的大锅摆在桌子中央,香气四溢。
“逐夜凉,”
他朝厨房喊,“再不过来没你的份儿了啊!”
米汤腾起的热气中,一个人影走过来,不是骨骼,朦朦胧胧的,正拿围裙擦手,一把干巴巴冷冰冰的声音:“不陪你,饭都不会吃了。”
岑琢抬手勾住他的脖子:“对呀,有你吃着才香嘛。”
桌边,哥哥姐姐轻快地笑起来……
缓缓睁开眼,雪白的天花板,一排七八个营养素注射瓶,还有医疗设备的嘀嘀声,岑琢尝试着坐起来,一动,床边的人忽然惊醒。
岑琢看着他,一个头发凌乱的男人,高级西装扔在一边,衬衫袖口挽到胳膊肘,一对黑眼圈,目光灼灼:“小琢!”
“哥……”
岑琢不敢相信,真的是他哥,失踪了十年的岑默。
汤泽的眼眶充血,红得有些吓人:“是我,”
他腾地站起来,朝门外喊人,“赶快,拿进来!”
小弟拿来的是一盘切成小块的桃子,用牙签插着,汤泽颤着手喂给他:“小琢,你说要吃的。”
弥留的话,岑琢记不清了,眼睛里的水闪动着,张开嘴。
桃子细心冰过,擦过舌尖,又香又甜,眼泪不争气地流下来,他赶紧拿扎满了针头的胳膊去挡,汤泽紧皱着眉头,迟疑地揉了揉他的头发:“是哥不好。”
二十一岁,伽蓝堂的会长,是大男人了,可在亲哥哥面前,岑琢哭得像个小孩子:“哥你上哪儿去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不来找我!”
汤泽用力握住他的手,心都要碎了,那个早上,炮火击碎了贫民窟的玻璃,面片儿汤泼了一地,姐姐的腰折断在椅子上,爸妈没有全尸,而岑琢,断着胳膊倒在血泊里,让人以为他死了。
只有汤泽,被冲击波震到门口,在垮塌的砖石下,看见了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一具暗黄色、抡双斧的组装骨骼。
他不要命地追上去,冒着炮火爬上它的背,在可怕的流弹中,在寒冷的空气里,他扒着它,扒得十个指头的指甲都没了,被裹挟进南下的流浪团大军,入关加入了狮子堂玄武分堂北府舵,成了一名御者。
“我给爸妈和姐姐报仇了,”
汤泽说,嘴角绷得肃穆,“那家伙死得比他们更惨,不只是他,所有参加了那天火并的人,无论男女,一个不剩。”
这些事,说起来三言两语,可从一个流浪儿到天下霸主,一个少年孤身一人追凶、隐忍、报仇,这中间有多少心酸、多少血泪,只有汤泽自己知道。
岑琢含着泪点头:“哥,你受苦了……”
汤泽安慰他:“这个年代,人生下来,没有不受苦的。”
岑琢颤抖着攥住他的手。
汤泽回握住他,低声说:“小琢,如果早知道是你……”
如果早知道,他会把半壁江山给他,哪怕是取消染社,改称伽蓝堂,只要能换来这个弟弟,他在所不惜。
可为什么,他到了最后一刻才知道真相?
因为须弥山,那个无所不知、洞察一切的“神器”
,它不许任何人在江汉提起岑琢的名字,尽管它早预见到了这个未来。
“为什么?”
岑琢昏迷这一天一夜间,汤泽问过它。
须弥山的黑色心脏徐徐旋转着:“我有我的原因。”
“你明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