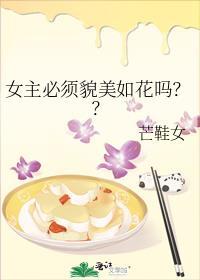第14章 李二柱我不怕你(第1页)
在那个偏远而被遗忘的乡村角落,冬日的寒风仿佛是来自地狱的咆哮,无情地席卷着每一寸土地。
李家的小院就像这冰天雪地中的一座孤岛,四周的土墙在岁月和风雨的侵蚀下,布满了深深浅浅的沟壑,仿佛是命运在这贫瘠之地刻下的一道道伤痕。
秀荷独自蜷缩在昏暗阴冷的屋内一角,那扇破旧的窗户像是一个无力的旁观者,任由寒风肆意闯入。
透过那模糊不清的窗纸,微弱而朦胧的光线艰难地渗透进来,却无法驱散屋内的阴霾。
秀荷的头如同一团杂乱的麻线,失去了光泽和生机,随意地披散在她那消瘦且毫无血色的脸颊两侧。
她的双眼红肿而凹陷,目光空洞而呆滞,仿佛那无尽的痛苦已经将她的灵魂抽离,只剩下一具行尸走肉般的躯壳。
泪水在她的眼眶中打转,却像是被冻结在了那痛苦的深渊,迟迟无法落下。
她身上那件补丁层层叠叠的粗布衣裳,原本的颜色早已被岁月洗刷殆尽,只剩下一片灰暗的混沌。
袖口和领口的磨损处,线头肆意伸展,仿佛在诉说着生活的艰辛与无奈。
那衣裳单薄得几乎无法抵御这冬日的严寒,却也是她唯一的遮羞之物。
她的双手布满了老茧和裂痕,每一道裂痕都像是生活在她身上划下的伤口,鲜血早已凝固,只留下一道道触目惊心的痕迹。
她的手指关节粗大而僵硬,那是长期劳作的印记,也是命运无情压迫的证明。
秀荷回想起那些如同噩梦般的日子,心中的痛苦如同汹涌的波涛,一波又一波地冲击着她那早已脆弱不堪的心灵防线。
清晨,当黎明的曙光还未完全穿透那厚重的晨雾,秀荷便被那冰冷刺骨的寒意从睡梦中唤醒。
她拖着沉重的身躯,艰难地从那破旧的炕上爬起,仿佛每一个动作都要耗尽她全身的力气。
她走出家门,踏入那片荒芜而贫瘠的土地。
田间的泥土冻得坚硬如铁,每一次锄头的落下,都只能溅起零星的冰碴。
秀荷的双手紧紧握住那粗糙的锄头柄,手臂上的青筋暴起,她用尽全身的力气,试图在这片土地上挖掘出一丝生机。
然而,无论她如何努力,那土地似乎都在无情地嘲笑她的徒劳。
她的脸颊被寒风吹得通红,嘴唇干裂,呼出的白气瞬间在空气中消散。
汗水从她的额头渗出,却在瞬间被寒风冻结,与她脸上的尘土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道道斑驳的痕迹。
“你这没用的婆娘,干活儿这么慢,想饿死老子吗?”
李二柱那粗暴的吼声如同一把利刃,划破了寂静的清晨。
秀荷的身体微微一颤,心中涌起一阵恐惧,但她不敢停下手中的动作,只能更加拼命地劳作,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暂时平息李二柱的怒火。
傍晚,夕阳的余晖如同一层薄薄的金纱,洒在这片疲惫的土地上。
秀荷终于结束了一天的劳作,拖着如同灌了铅般的双腿,缓缓向家中走去。
每走一步,她都能感觉到身体的酸痛和疲惫在不断加剧,但她的眼神中却没有一丝抱怨,只有深深的无奈和麻木。
当她踏入家门,迎接她的不是温暖的炉火和关切的问候,而是李二柱那充满厌恶和愤怒的目光。
“饭怎么还没做好?你这懒婆娘,整天就知道偷懒!”
李二柱一边骂着,一边挥舞着手中的木棍,向秀荷冲了过来。
秀荷惊恐地躲闪着,眼中充满了无助和恐惧。
那木棍带着风声从她的耳边划过,她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对不起,我马上就做。”
秀荷的声音颤抖着,仿佛是从牙缝中挤出来的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