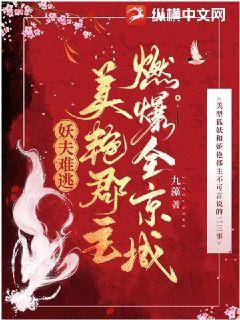第 51 章 051梦(第1页)
远在苏黎世度假的易思龄心情很沮丧,一晚上睡得不安稳,清晨五点就醒来,窗外还是一片寂悄的夜色,纯净的月光像泉水一样流泻。
十二月的瑞士,日出晚,天也冷,住在山中的城堡,世界只剩下冰雪与寂静。
她蹑手蹑脚地掀开被谢浔之的体温烘暖的真丝鹅绒褥,拿起昨晚脱下后就顺手搭在雪茄椅上的珊瑚色山羊绒浴袍大衣,套一双及膝长筒翻毛牛皮靴,对着镜子看了一眼,不太满意。
即使山羊绒大衣是Debturl现役首席设计总监亲自为她调配的独一无二的颜色,牛皮靴更是全球限量十双,但还得未免朴素,她又从抽屉里翻出一对祖母绿耳环一只带钻的隐秘镶嵌手表,离开时看了一眼在梦中安睡的男人,这才静悄悄走出卧室。
她一个人去了城堡的后山,坐在结冰的湖边发呆,心情恹恹,是花钱也哄不好的低落。
闺蜜昨晚告诉她,她儿子在港城和人恋爱了,爱得大肆旗鼓,爱得招摇过市,爱得轰轰烈烈,办一场赛马会请全港的名流,就是为了让人小姑娘出气,恋爱的对象是秦家的,不仅如此,还唆使着她妹妹一块骗她。
难怪最近三天两头看不到人,天天往南边跑。
想那孽障说了什么?
——“我喜欢漂亮的,看上去单纯却很有心机,她只能喜欢我的钱和权不能喜欢我这个人,知道我不好惹就要赶紧跑了找下家,找完了还要来克我。
我喜欢这种。
您帮我找吧。”
所以说,这可不是什么反语,这是正儿八经的真话。
一个看上去单纯却有心机的漂亮女人,爱钱爱权也罢,还广撒网有很多下家?还、还要来克他?喜欢上秦家的女孩,不就是来克他的?
天啊。
她命好苦!
易思龄对着空荡荡的深山尖叫一声,把头埋在膝盖里。
谢浔之刚来就听见了一声嚎叫,压了压耳根子,把带出来的披肩搭在易思龄身上,在她身边坐下,无所谓身下的草地还沾着清晨露水。
他柔声问:“怎么一个人跑出来?天都没亮,你来做冥想吗?”
易思龄闹脾气,扭了下身体,不准他碰她。
“盘盘。”
他叫她小名。
不应。
谢浔之只好又唤她“宝宝”
易思龄哀怨地抬起头,“你叫我王母娘娘都没用,你儿子要造反了。”
谢浔之笑了笑:“阿月怎么惹你了?”
“他谈恋爱了。”
“这是好事啊。”
谢浔之眸中闪过惊讶,“你不是成天盼着他交女朋友?”
“我是希望他交女朋友,但我不希望他交坏女朋友。”
“你都没有见过对方,为什么就觉得是坏女朋友?先入为主不一定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