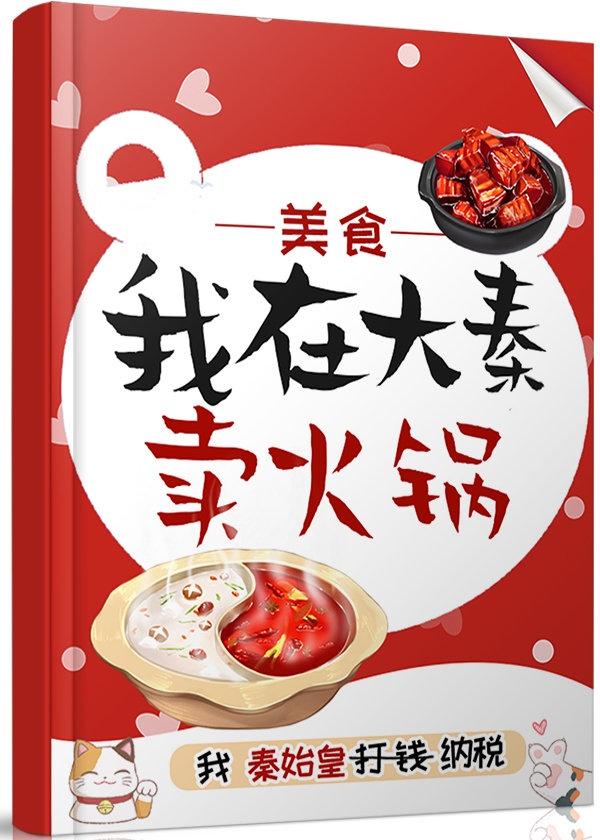二甲壳虫(第1页)
帷幔垂坠,彩绘玻璃半遮半掩,伯图斯子爵的画室浸泡在一泓蜜色的光中,活色生香。
西利亚神色惶急,银发汗湿,狼狈地粘在腮上。
他像只淋雨的雏鸟,直往丽莎大婶身后钻。
“我做不来夫人,我”
他嗫嚅着,双眼紧闭,“您、您没说要做这个”
他话音未落,画室里忽地爆出一蓬娇俏的嬉笑。
画架前是一片大理石台。
几条白腻rou感的小腿自台沿垂下,台面上,白绸凌乱堆叠,细滑得像是调羹搅出的牛乳纹理。
几个扯着白绸半遮半掩的美艳流莺窃笑着你推我搡,扭来扭去地破坏伯图斯子爵安排好的画面构图,翠青与湖蓝色的几双眼珠瞟向门口面红耳赤的西利亚,晶亮、邪气,像几条惑人的蛇妖。
画室四壁挂满伯图斯子爵的油画,靡丽、怪诞,穷尽手段地刺激官能伯图斯子爵醉心于描绘美人,无论男女,为满足这一癖好他从不吝惜花销。
“站过来,管事的马上就来了”
丽莎大婶用铁匠老婆特有的宽厚手掌死死钳住西利亚单薄的肩,粗声恶气道,“别他妈像个小妞儿似的”
“可是您说这儿招杂工”
西利亚被搡得直踉跄,狼狈地扯着领口。
“当模特,画一次五枚金图尔苏你得分我一个,当然了那也还剩四个,够让你带着你弟弟从贫民窟搬出去了,剩下的还能请几次药剂师。”
丽莎大婶压低嗓门,拿捏出一丝阴险的亲热劲儿,“杂工杂工一天才赚几个铜板,你不想给你弟弟治脑袋了”
西利亚习惯对外人说道文是他弟弟,这能省去反复说明情况的麻烦,况且,西利亚在心里确实是将道文当弟弟待的。
西利亚绞着手指,唇瓣翕动,面色忽红忽白。
“治。”
片刻后,他嗫嚅道。
如果那夜道文没冲进火场救他,那道文就不会受伤,更不会毁容。
与天资平平的西利亚不同,道文是个陶艺天才,老陶艺师年纪大了,干不了多少活,道文从十三岁开始就揽下了店里的主要活计,他做得又快又好,而西利亚负责打杂以及洗衣做饭。
除去圣像、壁画边框、刻印十字架花纹的浮雕等主要货品外,道文还擅长制作少女陶偶。
自然,小镇里罕有主顾舍得掏钱买这些小女孩儿的玩具,道文只是用一些边角废料做着玩儿。
可西利亚认为那些栩栩如生的少女人偶们皆透着一股曼妙的灵动感与勃发的生命力她们有着或柔润或玲珑的身段,以及肥鼓鼓的、可的小腿肚与藕臂,还有雪浪般松蓬蓬的裙摆。
她们用灵秀白皙的小手拈起一支鹅毛笔、一串白蔷薇念珠或一册羊皮纸诗集,猎手少女拉满异域风情的筋角弓、卖花女孩抛掷沾染晨露的鸢尾、女骑手跨上奶油色的阿哈尔捷金马那些绝不是平庸的陶艺师机械劳作的产物,与千篇一律的陶瓷圣像不同,西利亚愿称其为艺术。
上城区的贵族夫人与小姐们一定会上那些别出心裁的艺术品,道文那么英俊、那么才华横溢,若非为了救西利亚,他绝不会过上如此凄惨的日子。
“给弟弟治脑袋。”
西利亚梦呓般重复道。
画室女仆将西利亚的粗布衣裤叠好摞起,不知拿到哪里去了。
那几个美艳的流莺身着丝绸睡裙,洁白手臂或搭或挽,柔媚地攀附着子爵的肩头,嬉笑窃语。
西利亚攥着大理石台上的绸缎,拼命遮掩自己。
用来辅助构图的绸缎裁得细而长,挡不严,西利亚羞急地扭动,像枚丝蛹,薄而贴服的绸布将轮廓勾勒得清晰可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