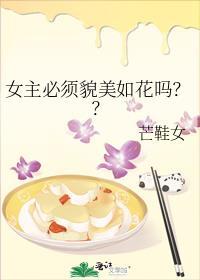第1章 十二点零五(第1页)
:“西南大路你走当中!”
没有漫天的纸钱,没有人摔盆,没有人打幡,我声嘶力竭的喊出了这一句。
可笑的是我知道出马仙入不了这轮回,我也没法和他说下辈子我们再见。
那天我收到了无数合作过的艺人、同行、搭档的微信,甚至还有带着哭腔表达不舍的电话。
虚情假意的背后我当然清楚他们怕的是什么,这顺水人情要做到死才叫圆满漂亮。
我静静地把陪伴了我和张嘉一十几年的两面神鼓和两把神鞭放到了阁楼上的箱子里。
十几岁时候我帮张嘉一挂上的神鼓飘带,如今已经满是斑驳,他从没换过。
又是一年雪花飘落,东北的天真冷啊,我掏出打火机,帮张嘉一点了一根烟,头也不回的走了…
假如你听过我的名字,或者看过我导的戏,那很高兴和你在文字的世界里相遇,若是初识,我也愿和你讲一讲在娱乐圈混迹多年的真实奇遇…
时间回到1993年8月31号,阴历七月十四,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一个晚上,坐标:黑龙江大庆,都说东北的夏天容易过,但这一年的夏天特别热,夏蝉似乎都憋足了劲儿在“大医院”
的树上叫个不停(现在那医院应该叫大庆油田总医院了,那时候大家都叫“大医院”
因为…挺大的…),闷热的天,深夜寂静的医院走廊,刚刚粉刷的绿色墙围子还有点呛人,妇产科的等候椅还没来得及粉刷,坐上去稍有晃动就咯吱咯吱的响,昏黄的灯光拉长了等候区的人影,医院的墙听过比寺庙更虔诚的祈祷…
这一撮人在产房门口坐立不安的等待着产房里的消息,在这群人中,一个四十多岁烫着大波浪的中年妇女,和这群焦躁的人相比明显状态不一样,悠闲的靠着靠着墙角,时不时的瞟着几眼表,一会儿又叹了口气,明显是等累了。
“我说大霞,你坐会,我看你站这么长时间了,坐下歇会儿”
椅子上的其中一个老头站了起来,把椅子让了让。
“对啊,别光站着了,坐下喝口水”
边上的老太太赶快站了起来,拿了一瓶水递了过去,这俩人也不是外人,我姥和我姥爷…
“叔,姨,没事儿啊!
咱们都楼前楼后的住着,小芳这生孩子,我妈特意嘱咐我今天可得全程陪着,这出生时辰可得记清楚!”
大霞马上调整姿态,立刻露出塑料花一般的笑容。
“大霞啊,姨不懂,你妈说今天这日子是不是有啥讲究啊?”
我奶接过话,又偷偷的瞟了一眼我爷,生怕我那啥都不信的爷爷批评我奶封建迷信。
“姨,倒不是有啥讲究,我妈让我来就是记个时辰,主要平时也就算了,今天这日子赶的…也挺好!”
大霞虽然平时是“大了呼吃”
的一个性格,但话到嘴边,看了一眼我爸,又咽了回去…
“啥日子?现在每天过的都是好日子。
想当年…”
“可别想当年了,你当年…”
我奶一下按住了要起腔调的我爷。
咱们就说也就是寸,话还没说完,这闷热的晚上又忽然开始打闪,闷雷哄哄的响了起来,雷声打断了大家“没话找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