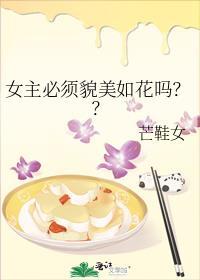16为什么喜欢我H(第1页)
徐明隗停步时钟栗没搞懂他想做什么。
两人先是在附近的兰州拉面店填饱了肚子,又去附近的小花园闲晃半小时。
离天黑还早得很,钟栗正想着不然别管什么天黑不黑直接撬锁进去吧,要么索性先回家,半夜再来,接着撞上男人后背。
“怎么突然停下来?”
她揉揉鼻尖,费解地问。
他回身看她,眼睛里装着令人无法忽视的色彩——期盼、渴求,以及那么多的……欲望。
钟栗不自觉轻轻打了个寒战,扭头一看,街道内侧的是一家小宾馆。
为何会走到这附近,恐怕不是什么巧合。
“你想做什么?”
她声音立刻弱下去,“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在干嘛?”
“我知道,在调查。”
他握住她的手,碰触而来的掌心微微湿润,带着些许潮气。
“这几天你很忙,接下去也会很忙,对不对?”
这是事实,钟栗无可奈何地点点头:“那也不是做这种事的时候……你怎么这么饥渴?我什么都没带啊!”
后一句她踮起脚俯在他耳边低低说,热气扑到耳侧颈窝,轻轻的,像是在啜饮他的气息。
“用你的手就行。”
他耳尖红了,眼神直勾勾的,像迫不及待地想要把她吞进身体。
钟点房自然是有的。
阳光高照的午后,前台服务员打着哈欠,都没多看两人一眼,甩来一张门卡:“叁楼307,电梯左拐。”
趁徐明隗淋浴的功夫,钟栗把买来的啤酒和矿泉水在小方桌上摆好,又拉开床头柜。
里面什么都没有,想来也是,毕竟是正经宾馆。
和得了强迫症一样,她又去挤出洗手液,在掌心揉开,细细搓洗每一根手指,然后冲干净。
钟栗在这边坐立不安,浴室里的徐明隗甚至在哼歌。
没听过的调子,很古朴,像什么民谣小调。
他唱歌很好听,声线比平常说话低一些,干净,清澈,与水声融合,模模糊糊,紧紧抓着听者的耳朵。
Alpha出来时没把身体完全擦干。
水浸润富有弹性的、饱满的肌肉。
它们不是在健身房里练出的大块腱子肉,而是强健紧韧的实用性肌肉。
他用穿着衣服时完全看不出来、充满生命力、热切温暖的肉体包住她。
他身上的热气侵犯进大脑内总是冷静的那块地盘,她昏昏沉沉地,将脸紧紧贴住蒸着水汽和热量的橄榄色胸肌。
徐明隗就那么抱着她,笑个不停,低低的笑声顺着胸腔震动传遍她的。
从胸口到胳膊到腰腿,钟栗清晰地感受到它们在慢慢变软。
他勾着Omega的手指挪到腰间,一挑,松松围着的毛巾就顺着腰线滑落。
一副迫切期待着被她光临的腰身,如此充满情欲,直截了当,令人脸红。
钟栗的手指进入他的生殖腔,两指轻易分开湿润渗水的肉缝,压着最底下略显粗糙的肉壁慢慢蹭进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