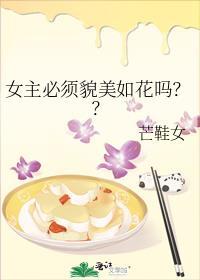子安难觅白欢肆中(第1页)
一
宁欢在宋府的日子也还算好过,吃了几次闭门羹的小丫头不会再来打扰这份清净。
即使一开始纯真无邪又能怎样,那样的环境里,那些风言流语入耳。
就像一层层染料,最后都会染成一样的颜色,与她不同的色彩。
“她们总说我自命清高,出身不详却还要装作这样……”
宁欢看着旁边那个跟了她许多年的侍女,那侍女因为先天哑疾,被打到她这里伺候。
侍女摇摇头,比划了很久的手势,又急忙将桌上那块栗子酥递给宁欢。
宁欢笑着将那块栗子酥掰了一半,让侍女吃。
侍女犹豫了很久,小心地用手托着,一点点吃掉那半块栗子酥。
很甜很甜真的很甜,是她尝过的第一种甜味。
宁欢翻看着那本话本,听说是最近人手一本的新潮。
贺子安寻来给她解闷,说她整日闷在屋子里也不是办法。
宁欢最近许是弹琴弹久了,总是觉着无力,有些头晕。
窗子微开,月光倾斜一角,灯花也落霜一般似的皎洁。
宁欢走到窗前,月光顺着掌心的一道道纹路流动。
院中的枇杷树簌簌摇起清风,侧耳倾听,风声若乐音。
抛却那些烦恼,不做什么淑女,一生活在世人的评判中。
史书寥寥几笔带过一个人的一生,几十年落笔一行都算多。
二
宁欢日渐消瘦,苍白的脸浮着病态的红晕。
隔着浓雾般的纱幔,隔着摇晃的珠帘。
宁欢在这个春日突然病的起不了身,高烧不退。
贺子安隔着许多人,与她草草见上一面。
她的眼那么远,那伸出的手只能触碰到冰冷的窗棂。
她的泪从眼角滑落,融进听不清的梦呓中。
大夫皱着眉开了几副汤剂,让宁欢切记莫要忧思过重。
宁欢似乎是从连绵的昏沉中挣扎出来,那些雾气散开,她伸出手想要抓着什么,那手悬在半空中虚抓了几下,随后又轻飘飘垂落。
就像是一只想要还巢的孤鸟,失了方向,慌乱惊惧之间被弓箭射中,从空中直直坠下。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进补,她苍白的脸色泛起了正常的红润。
她爱在那棵枇杷树下弹琴,那窗子里透出的光亮让她想起那个漫长近乎失去尽头的梦。
枇杷树摇动的风声,将微暖的春日变作了初夏。
宁欢像是恢复了健康,于是贺子安邀约等过些时日去赏荷。
宁欢兴然应允,暑气一点点将春日那些微暖扬起,让人拿起搁置的扇子,穿上那些轻薄的衣裙。
宁欢梳起髻,粉色的带显露难得的少女心思。
她打量镜子里的自己,很少这样娇俏打扮。
她平日里穿的清素,这样打扮也还算让人眼前一亮。
之前病了许久,如今这样坐在镜子前梳妆一会儿,便有些疲累。
宁欢穿上那件樱粉色花裙,妆匣中一支菡萏玉簪被轻巧地拿起,缀在梳成的双平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