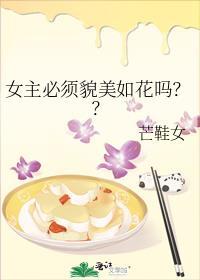第九章 徐离道人(第1页)
转眼,我看向窗外,我听见鸡叫了,太阳好像也出来了。
早晨的阳光却像中午的烈日一样耀得我的眼睛一直晃,我慢慢地移到窗边,试着用手去接着这一生中最后的日光。
但是这日光对我并不友好,它就像滚烫的开水似的烧的我的皮肤直冒白烟。
原以为昨晚一夜在灯光下的适应,我已经不怕光了,如今才知道与阳光相比,灯光根本算不了什么,也不得不暗自嘲讽一把:现在,我竟是个见不得光的存在了。
陆陆续续的开始有很多人在我家进进出出,大门上挂上了白布,客厅里设了灵堂。
爸爸把我以前的学习桌搬了出来,摆上了我的照片、香烛和我爱吃的水果,我猫在没有阳光的拐角,看着照片上的自己,我没有再哭了。
家里来了很多亲戚,大部分我都记不清了,有些连名字也忘了。
他们有些人安慰我妈妈,有些人安慰我爸爸,有些人在谈话聊天,有些人在喝茶玩手机。
有些人感叹我去的太突然,有些人惋惜我英年早逝,有些人表示要以我为戒,有些人说我去的太过凄惨,也有人表示跟我并不熟我没有感动、没有悲伤,也没有愤怒,只木木地蹲在角落里呆愣愣的的一动不动。
直到有一道光晃了一下我的眼睛,我下意识的伸手去遮,却发现那光竟没有穿过我的手照到我的脸上。
要知道,不管是灯光还是日光都是直接穿透我的身体并灼伤我的。
可是这道光却并不刺眼也没有灼痛感,我有些兴奋,抬头望去就看见一个女人正领着一个穿着长风衣的长发男人在和我爸说话。
没来由的,看见穿风衣的男人我就特别的厌恶,甚至想上前把风衣扯下来撕碎。
难道我的死和风衣有关吗?可是我已经记不得我是怎么死的了。
话说回来,这个正和我爸爸说话的女人又是谁啊,看着她一脸严肃又悲痛的样子应该是我亲近的人吧。
我想听听他们说什么便猫着腰凑近了他们,可我刚一靠近,那个穿风衣的男人手腕上的铃铛便响了起来,那个铃铛的声音有些刺耳,刺的我耳膜直疼,我赶紧捂住了耳朵退回到了角落里。
可是那个男人却好像察觉到了什么一般,竟转过头来看向我的方向,是的,他的眼睛正盯着角落里的我的眼睛。
我愣住了,他,他能看见我吗?不,不会的,不可能。
虽然极力的说服自己说不可能,可是他下一个动作却让我啪啪打脸。
他伸出另一只手覆盖在带铃铛的手上将铃铛捂住了,然后,他冲我笑了笑。
我发誓,他真的冲着我笑的。
我觉得我可能要被他吓死了,虽然我已经死了,但是他也死了吧,否则怎么能看见我的?那这个死鬼想要干什么,跑到我的家来,还站在我爸爸的旁边,他很危险啊!
不行,我要救我爸!
怀着这样英勇的念头,我再一次挪上前去,可还没有挪到旁边我就听见了那个女人对我爸说的话:
“姐夫,我给你介绍一下,他就是徐离道人。”
说完还用手示意了一下穿着长风衣的这个男人,男人上前一步,微微颔首道:“程先生,你好。”
姐夫?!
我愣了片刻,这个女人是我小姨妈?
这时三叔过来了,三叔站在爸爸一侧正好挡住了窗口斜射进来的阳光,我趁机蹲在爸爸和三叔之间,谨慎地盯着面前的这个“徐离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