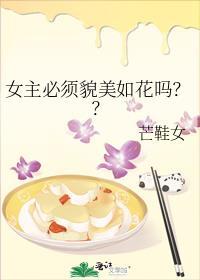第155章(第2页)
“殿下!”
男子三两步跑到我面前,眼眶微红,欲言又止,一副想哭又不敢哭的样子,着实教我有些尴尬。
虽然已经知晓了对方就是傅若蓁,是我名正言顺的王夫,可是于现在的我而言,他更像是一个素昧平生的陌生人,空挂着伴侣的名头,却没有半点熟稔的印象——真要说起来,自我失忆以来,最熟悉最亲昵的人,也只有邝希暝一人罢了。
按理说,王夫才应该是我最亲近的人。
控制住自己想要回头去寻邝希暝的念头,我伸手虚扶了一下有些踉跄,看起来就要倒进我怀里的王夫,在指尖刚触碰到他的一刹那又忍不住收回了手——感觉到他与我都不约而同地顿了顿,也是讶然。
我也没有料到自己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像是无法忍受对方的触碰一般……可我分明是自失忆以后第一次见到王夫的模样,对他也并没有什么恶感,又怎会如此呢?
看着王夫眼中显而易见的受伤与落寞,我有些歉疚,却又不好再突兀地伸手,只能换个方式补救,落下的手转了个弯,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肘:“嗯……节哀。”
话才要出口,却又不知道以前是怎么称呼对方的,只好掩饰性地略过这一茬。
——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失忆这件事,王夫究竟是否知情?
若是他知情也就罢了,若是不知情,那我又是否能告诉他?
这背后有什么利益牵扯,一时半会儿也无法分析透彻,看来还是要等抽个空与邝希暝合计一番才好。
想到这儿,我不由又是一愣:自己似乎不假思索地便将邝希暝划归到了可以商量可以信任的那一方,甚至于对她有些莫名的依赖——然而依照种种蛛丝马迹来推断,她与我的关系可是扑朔迷离,远非三言两语能解释得清,也绝不是单一的是非爱憎能够概括的……至少,不仅是同母异父的姐妹那么简单。
原想着,因为广安县主的缘故,我本该对她心存戒备才是,可恰恰相反,我就是没来由地想要相信她,想要依靠她,乃至于……想要亲近她。
无关对错,不可理喻,只是想这么做。
我明白在诸事未明的情况下,不能再这么放任自流下去,可每每触及她那双藏着复杂情绪的眼眸时,我便不由自主地心软了——不知道失忆前的我对待她的态度能否强硬,但是现在的我却根本无力抵抗。
大概,唯一的办法也只有尽可能避开这双教我无可奈何的眼眸了吧。
“多谢殿下关心,奴无碍。”
收回对于邝希暝的遐思,就见王夫朝我福了福身,冲着我微微一笑,眼中是强自压抑的悲伤,“殿下一路舟车劳顿,奴已经吩咐仆从备好了热水,请殿下洗漱休息。”
“你有心了。”
我叹了口气,正打算再劝慰他几句,陡然间觉得浑身一凛,如针芒在背,将我还未出口的话生生卡在了嗓子眼——皱着眉头侧眸看去,却是本来一直将自己当作布景隐藏气息的邝希暝正幽幽地盯着我。
准确地说,是幽幽地盯着我的右手——刚才扶过王夫手肘的那只。
这个表情,不太妙啊……
随着我的目光所及,王夫也顺势看去,他骤然变换的面色教我心里一咯噔,有了不好的预感——王夫定然是认得身为皇帝的邝希暝的,忽然间发现本该在帝都观澜执掌天下的九五至尊却出现在千里之外的小城之中,更是屈尊纡贵扮作了侍卫的模样……这其中的缘由不得不令人玩味。
幸好王夫是正对着我,背对其余诸人,惊色一闪而逝,很快便镇定下来,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教我暗暗松了口气——眼角的余光则看到邝希暝紧扣着剑柄的手指并未有丝毫松懈,才刚舒下去的一口气又提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