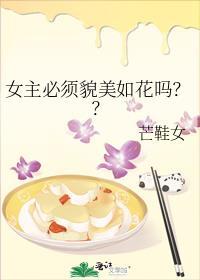26 第十五章(第2页)
待取衣裳侍女,见娘子神灰败得像覆了层尘,柔弱身躯似连说句重话都起,由得把脚步和声音都放轻了许多,踌躇道:“娘子现在可要更衣?”
文令仪如梦初醒,“嗯”
了声,走到了屏风。
她木然地由着侍女解开衣带,褪下寝衣,神落在屏风一角蝠纹上,久挪动半分。
侍女极小心地打开衣襟,正要褪下,&xeoo吓得愣了。
只见目所及皆深红痕,重力弄出朵朵红梅艳丽过头,便连纤长双也未能幸免,通身余下一块好。
咬痕揉痕,显然男子留下掌痕,些知弄出痕迹,像普通欢好就能。
可明明听说,郎君昨夜歇在书室,那……
她惊骇地停下了手上动作,看向娘子,声声心跳如雷。
文令仪将衣襟紧紧拢起,哑着声,要她们都出去,“要声张。
衣衫留下,自己换。”
原难堪,更加难堪处境等着她,仅要强忍着去湢室洗刷去身体深处残留异样,要在侍女面前露丑,再亲手遮掩掉他在身上留下痕迹。
忍耐着穿好衣,又觉前涨得厉害,感受了下,最里层小衣叫凭验系得太紧,也许在过去刚好,现在&xeoo过分紧绷。
文令仪木着脸,重穿了次。
恰好钟儿将马车安排好了,就停在仪门前面,自己飞奔,在窗下就迫及待地开口。
文令仪穿着刚换好衣裙,匆匆掠过屏风,朝仪门而去。
过庭院时,她现廊下摆了八九个兔子样式花灯,被屋外凛风吹得外糊纸片直响,由自主慢下了脚步。
“娘子,郎君上时可用心了,长庚说,明角风灯里油烛暗了,画错了一笔,郎君就将整张纸……”
钟儿笑道,直到觉娘子怔得厉害,慢慢止了话头。
“去郊外。”
文令仪转过身,敢多看,步子迈得更急了。
到了几天前造访过送行亭,寒风凛然,落了地绿松针,意料中地看见熟悉影。
冷风扬起文令仪裙角,她站在亭子美靠前,目光放远,看着延伸到天尽处坦阔官道,怅然若失。
错过了短短一两个时辰,竟就能叫异地得见,只能看见样凄凉。
原时辰对,就算她到了郊外,也及。
会在原地一直等她。
也许,就她宿命,总会失去最珍视,行尸走地留在想留下地方,求生欲,求死能。
想着,身上又开始难受了,被拓拔宪碰过各处让她刺痛,真想管皮都削了去,血流而死也好,只剩下一具骨头也好,至少那骨头干净。
他脏手染过血,又碰了她,她算什?委身敌寇娼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