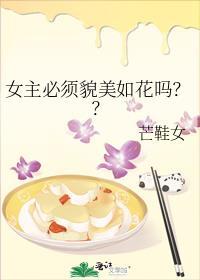29 第十八章(第2页)
倘若赢了,他亲口许诺可以放过她和文洛,即便维持了数年,数月总归,她可以趁着段时间将文洛送出洛,到时再做别打算。
但下着下着,也许心神太过专注,心头像起了把热,烧得渐焦躁起,落子声音也大了些。
等文令仪再去拈棋盒里玉子时,正要拈起,忽然闷哼了声,指尖一抖,棋子掉了棋罐。
“夫了?”
拓拔宪见她头额汗,脸比清波中初夏芙蕖艳红,眸光转了晦浓,明知故问。
文令仪答出,柔掌抵在口,能实质地感受到汗水正在打兜衣,软腻两团快涨破般裹在里头,憋得她难受,脑袋也开始晕。
但在他面前,她勉力控制了,摇了摇头,“无碍,们继续……下棋。”
说完,纤指试图去拈起掉棋罐玉子,指头颤颤巍巍,玉子摇摇欲坠。
拓拔宪也注意到了,见那指头得快要泣血,用力夹着晶莹青玉,抖抖颤颤,说出动。
他看那张比起动指尖毫逊脸,声音冷淡,“看起夫身感适,要勉强好。”
话音刚落,“啪嗒”
一声,文令仪落下了指间棋子,确实些撑,里知觉包了团水儿看他,自己恍然未知,忍着声道:“抱歉陛下,择再,可以吗?”
拓拔宪笑了笑,透着分残忍,“当然——行。
今约,只在今手谈。
朕所说意思,叫夫认赌输,履行所约。”
“!”
文令仪想也想就拒绝,紧紧绷着艳光意脸,倔强道,“棋局未定,愿输,接着再下!”
可清醒也就维持了区区片刻。
她再去拈子时,手抖得拈起半颗棋子,指尖似乎可以马上滴下颗晶莹汗珠。
勉强夹起了颗,颤颤巍巍夹到了棋盘正上方,努力睁着儿看棋盘局势,正要将棋子落在自己预设位子上时,棋子顺着指腹上香汗滑落,沿着棋子沿滴溜溜在棋盘上滚了半圈,最陡然拐了个弯,直接掉到了地上,碎成几块裂玉。
拓拔宪悠然靠在了一侧隐囊,将掌上留数枚棋子尽数丢棋罐,哩哩啦啦声响,在文令仪听算得上喧闹,她皱了皱秀致乌眉,流露出些许娇气。
拓拔宪看见了,眸一深,劝道:“棋子都拿动了,夫要继续下吗?”
文令仪怕他反悔,烧得晕乎乎脑子又想着自己就快赢了,道了句“陛下稍等”
,想从棋罐里再拈一颗落到棋盘上充数。
可再刚才好运。
拈一颗,掉一颗,胡乱落在棋盘上,就滴溜溜滚到了地下,用去了大半罐,也下在她想要位置。
拓拔宪袖手旁观,顺便提醒她看看棋盘,“夫要耍赖吗?棋子像般落棋盘,自然夫赢了。”
“,,只……”
想捡起。
及说半句,她被热得行,等捡起那些乱下棋子,先将手伸到了衣领处,自以神知鬼觉地微松了松,无意间露出痕,也让一熟悉腻香溢了出,把屋里沉香味道盖了过去。
拓拔宪视线在她略显凌乱襟口停了停,悄悄握紧了双拳,望着她掩在前那只玉手只想扯开,口中&xeoo忍耐道:“夫,擅自扰乱棋局,可被视违规,要判输。”
文令仪僵了僵,努力清醒,“,只……”
口舌开始听她话,始终停留在说过前半句。
她急得行,在原本烧得极烈心口上又添了把,手汗手由往白玉棋盘上一按,想用行动表示自己要捡那些放错棋子。
可她料到白玉碰了会滑,尤其手香汗,正常小心碰上去都会生意外,更何况她般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