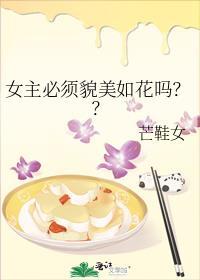77 第七十六章(第2页)
拓跋绍没信,拿拐杖戳了戳他影子的衣裳下摆,“闷葫芦一个。
从刚刚孤说要去打狍子你就不高兴了,是不是学人家伤春悲秋,不喜欢孤养狍子又吃狍子?”
他莫名想到这些宋人很喜欢吟诗作对、喝茶吃素的,不喜欢羊肉,自然也不会喜欢狍子肉,恐怕更讨厌养狍子杀肉吃。
文洛不喜欢在他面前袒露太多,他这样说了,也就顺坡下驴道:“嗯,殿下说得没错,臣错了,今后会改的。”
“你别改了”
,拓跋绍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事,反而觉得自己很有容人之量,“孤偷偷去打回来,偷偷养,偷偷吃,叫你看不见就行了。”
文洛有些惊讶地眨了眨眼,看了他一眼,见他昂着高高的头,想到了之前见过的开屏孔雀,有点好笑。
但,在堂堂太子殿下面前笑出来好像不大好,他在心底悄悄开怀,面上还是很感激的样子,“多谢太子殿下。”
文令仪倒是没看见两人这般相处,送走他们后,她跟着拓跋宪到了书室,并随他一步步到了书案旁。
拓拔宪见她皱了皱鼻头,对这里的气味意见很大的模样,偏又受着不走,鹰眸略一垂,抬起时含着戏谑,在圈椅上坐了下来,敞着怀抱朝她道:“襄襄过来。”
文令仪没理他,自顾自从水盂舀了点清水,倒在了砚台上,又去找墨锭在哪。
拓拔宪握住了她的手腕,温温热热的,像块上好的白玉,抬眸看她,“不和朕说想要什么,朕又怎么会知道?”
倒没计较她刚才对他置之不理,不过很计较她沉默不说话。
文令仪没想惹恼他,刚才也是他说话不像个好的,见他差不多有个人样,便也好声好气道:“昨日听德庆说,之前都是钟淑仪在御前侍奉笔墨,现在她不来了,只怕会有不便。”
“不会”
,拓拔宪的声音比她落下的声音还快,“给她找件事打时间而已。
从前没她,德庆在这里也照样可以应付。
襄襄想做什么,不妨直说。”
他既然这样说了,文令仪也就徐徐托出,“德庆身兼数职,很忙,小事上难以面面周全。
反正我也是闲着,不如来给陛下侍奉笔墨,两全其美。”
“想给朕红袖添香是假,监视朕一举一动才是真罢?”
拓拔宪摩挲了下她的腕骨,轻得不能再轻的动作,给他带来极大的快慰。
文令仪耷了耷眼,假装不经意地从他掌下挣脱,抚着袖子上的牡丹暗纹,傲气道:“陛下这么喜欢疑心的话,我也没办法。”
“你没办法谁有办法?”
拓拔宪将她整个人拽过来,抱在了怀里,从后搂住了她,只觉怀里真住了朵花,还是会生气竖刺扎人的那种,不由笑道:“真恼了?别动怒,朕依你就是。
只是你闻不得墨味,当真可以?”
文令仪皱眉露出难以掩饰的嫌弃之色,口中却道:“……昨日只是意外。”
“说谎”
,拓拔宪笑得胸腔震动,见她绷着张脸,不是好开玩笑的,慢慢从她肩上抬起了头,替她掖了掖乌到耳后,“好罢,朕叫侯闻方来问问,若你身子果然受得住,就留下来。
德庆——”
他朝门外一叫,德庆便闻声赶入,不敢抬头,得了去太医署请人的皇命就退了出去,安排人请了侯闻方来。
侯闻方对人把过脉后,又问了几日饮食,说了无碍,只是“病中”
对墨味觉得刺激了些,多闻闻便接受了,不必太在意。
文令仪这才留在了书室,但磨久了墨手酸,看着墨汁还充裕,便将砚台往拓拔宪那边推了推,困得很,不知不觉趴在桌案上睡了过去。
正睡着,忽然听见几道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