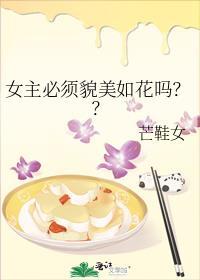六一八 举世无双二(第4页)
夏君黎却笑道,“所以你那时——全无疑虑便肯帮我。”
邵宣也没有回答,好像倦了似的,只挥了下手,算是辞过了,径出门去了。
屋中俞瑞听刺刺叙讲了一年未见,如何单疾泉和单无意竟都已隔了阴阳,夏君黎回来时,只见他苍老面上此时竟也有黯然。
“还是老夫命长啊,”
俞瑞慨叹着,“世事难料,能活着竟已算是很好了。”
“君黎哥,”
刺刺见他,便捧起东轩门那叠录书走过来,“我方才都看过了,邵大人说,旁的都同往常一样,就今日下午有个戏班进来,去太子府上的,这里头的人他不尽晓得。
这戏班二十多个人呢,申时进来的,到徐大人送这记录来还没走,要不要去问问?”
夏君黎取过来看了看,一旁俞瑞却忽然笑出了声。
夏君黎侧目看他:“有何可笑?”
“我只是想不出——瞿安能做这种事?他这样的人,会易容躲在戏班里?想着不可笑么?”
“他躲在朱雀山庄做个男宠,想着便不可笑?”
夏君黎反讥得毫不避讳。
俞瑞面上笑容顿失,就连刺刺都忍不住拉了拉他。
“我并非说笑。
在我看来,他能忍受这世上大部分人都不能忍之屈辱,能做出这世上大部分人都做不到的事,躲在戏班子里如何不可能?你可知东水盟那些人,一向也都喜作伶人戏子模样的,或许正有瓜葛。”
夏君黎将录书抛到桌上,“俞前辈如果真想替他洗脱嫌疑,与我一道寻出真相方是智途。”
他还是与刺刺商议了下。
戏班自不是不可疑,但此时夜色既深,去太子府实是挑事的意味过重。
四门不开,戏班最快只能明早再走,倒也不必定要这个时辰欺过去,不过夜长梦多,若真是瞿安这等高手混迹其中,亦不知一夜之间会做出什么事来。
他便先着了亲卫之中一小队人打着巡夜之旗号去往太子府附近留意。
话说回来——他心下明白,这一来自然也是因为张庭这事失之草率,以至于他不大好在这当儿再去得罪赵眘最纵容的这个太子,授人以柄;二来,他亦并没有太大的把握,那戏班就定有什么问题。
东轩门虽然同东宫在一个方向,可这些有资格入内城来的戏班,一向都是熟面孔,约束颇严,易容顶替就算可行,独溜出来却并没那么容易——开四门时戏班还没走,打伤单一衡的人又定在东轩门内等着门开的那些人之中,无论怎么想,要把这两件事硬扯到一起都有些牵强——比适才硬指张庭还牵强,就是自己都觉得这回是自己更像那个无理寻衅的。
他另派了人去往四门,交待了倘天明戏班出去,务必严查细核,可心里终究还是不那么有信心,不免颓颓唐唐地在桌边坐下来了。
“一衡还好么?”
他问了一句。
刺刺答道:“没大碍,他这会儿睡得正好。
鬼使伯伯也去瞧过了,说只是有些虚,没事的。”
“一衡……是被极阴内力所伤,以俞前辈所知,瞿安之内力,是什么样路数?”
俞瑞听他还是纠缠于瞿安,原本又想笑——瞿安只是天生长相稍嫌有些阴柔,但招式内力一向都与“极阴”
二字沾不上边,他甚至想象不出瞿安出手阴柔是何光景。
但料想如此说又要被夏君黎抢白,不免哼了一声:“我便说他不是这个路数,你又不信我。
纵然信我,你也要说,他二十一岁离开黑竹之后,谁知道生过何事,又学过什么新的内功心法。”